
读《康熙的红票》
第一部分 进入清朝权贵圈的西洋人
欧洲的传教士是在明末来到中国的,其主要是耶稣会成员。
在明代,他们进入中国的主要方法,便是通过与士大夫进行交往,意大利籍耶稣会会士利玛窦,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为了在中国传播天主教,就必须找到进入中国的切入点,这就是红衣大炮。在明末局势下,大炮在战场上发挥了超乎寻常的作用,而当时又只有洋人可以制造,神父们通过大炮生意,开始进入到两翼的政局之中。
明末清初中国的战争形式再次出现了巨大的变革,一个突出特征便是西洋大炮的引入,成为了有效杀伤敌人和攻城的利器,特别是在少数民族社会中,军功是取得社会地位的重要途经,汉人在操炮上的优势,也使得汉八旗的出现,炮兵也成为了特殊部队。孔有德的带着大炮精兵投奔也使得明朝炮兵与清军骑兵之间的平衡被打破。
最初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多习汉语,并不通满语。一部分与清军合作的传教士自然而然就和佟家这个汉军旗的代表性家族产生了连结。而康熙的母亲的娘家,恰恰就是佟家。
在清代,除了君臣关系之外,还有满族内部的“主子与奴才”之间的关系,奴才被主子视为是自家人,而相当一部分传教士可以康熙年幼的时候,就对其施加影响,康熙对于传教士的信任不应当源于对西学的兴趣,应当是先信任传教士,再对西学产生兴趣。 古往今来只有长期接触皇帝,首要条件便是皇帝的信任,只有皇帝信任,才会和他们接触,进而传播学术与技术,最终才会产生兴趣。
这些传教士被安排在内务府之中,而非主管宗教事务的礼部,之后康熙朝一系列与天主教相关的事物,几乎都由内务府来主持,这是皇帝的自己人。
传教士选择了上层路线,不可避免的就会被卷入到朝堂斗争之上,清初政局的满汉斗争是一条重要的主线,而早年来华的传教士与汉族士大夫交往,学习汉文化,不自觉的一批传教士(如汤若望)等就成为了汉族士人的代表。
应当说,在满人看来,传教士和汉族其实差不多,只是一个稍微特殊一点的外族罢了。传教士得以立足于政坛的一个优势便是其掌握了比较先进的天文学知识,得以在钦天监立足,钦天监除了观测天象外,更重要的是解释天象,在关键时刻会发挥意想不到作用。
在当代的研究中,杨光先被凸显了出来,进而被理解为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与碰撞。历狱事件始于1664年,当时辅政大臣执政的第四年,辅政大臣打压汉官汉制的大背景下,杨光先参劾汤若望及其天主教谋逆,导致全国各地的传教士被押送京师接受调查。事实上,时人对于杨光先的评价并不高,双方结怨,也是因为传教士掌握的钦天监修改了星宿,使得众多算命的技术遭到了冲击。
历狱事件改变了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播策略。传教士意识到算命风水领域存在风险,决定避免涉足,并转向满人权贵圈层作为主要目标。康熙亲政后,南怀仁掌管钦天监,仅进行天文观测而不碰测算部分,这也反映了康熙对满人统治地位的巩固。
第二部分 红票与中西交往
在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谈判之中,传教士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康熙派出了自己的两位亲信传教士,担任实际上的谈判代表,他们更加了解欧洲的国际关系与交往原则,深知沙俄陷入大北方战争中不能自拔,不可能在东方再启战端,他们精通拉丁语,而且忠于清王朝的利益,甚至比满族王公的态度更加强硬,甚至被彼得大帝认为是背叛了基督教世界,将耶稣会教士赶出了俄国。
在传统的塑造中,康熙被视为一位自大的君主,作为异教徒强有力的干预了“中国礼仪之争”。但作者认为,这也在很大程度是“历史的书写与记忆”这一问题所造成的。传教士被康熙视为自家人,教会事务由内务府而非礼部主管,在接见俄国和教皇的使团时,为了绕开朝堂内部对于觐见礼仪无休止的争论,采用“家宴”的方式进行招待,因而在正史记载中并不多。传教士们所撰写的《北京纪闻》为了向教皇施压,必须要表现出康熙对于“中国礼仪之争”的态度,事实上康熙只是在支持这些陪伴在他周围几十年的传教士而已。
多罗使团发布的禁止中国礼仪的谕令直接与康熙的立场相冲突。康熙对此采取了灵活的应对措施,例如让五位传教士在广州待命,等待康熙派遣的使节回来后再作进一步商议。
康熙与教皇使团之间的交往充满了复杂性。康熙在处理这些外交事务时既表现出耐心和灵活性,又显示出对教皇使团某些要求的不满和质疑。这种态度反映了康熙在维护清朝主权和文化传统方面的坚定立场,同时也体现了他在国际交往中的务实策略。
第三部分 荣耀后的沉寂
教士在中国政坛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和皇帝之间的特殊关系,因而教士对与皇子们也积极投入,联络感情,希望可以得到新君的支持。
康熙两次废立太子,最终在晚年出现了津津乐道的九子夺嫡的戏码,传教士也是穿行其间。朝廷也逐渐分为了废太子,皇三子,八子和雍正四派。
实际上雍正即位超乎了当时大多数人意料,传教士们对他也没有倾注太多的关注,而雍正对于佛教更感兴趣,而且在修行水平上也异常的高,雍正皇帝在年轻时便开始接触佛教,并在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与名僧超尘禅师开始深入交流佛法,这表明他从二十岁左右便已开始修行,并且其修行水平得到了佛教内部的认可。
雍正皇帝的佛教修行不仅限于个人修行,他还指导了许多僧人和信徒的悟道过程。例如,他指导了扬州高祖第一代祖师天慧彻祖,并且他的佛教著作被中日两国的佛教界广泛收录和出版。
实际上雍正对教士们的仍然抱持这实用主义的态度,但仅希望借助其力量,而不希望干预政治。此后仍有教士来华,蛰伏于宫廷之中,服侍两侧,静观其变,如画家郎世宁。欧洲的教廷也发生了巨变,耶稣会被解散,留守北京的教士们可以得到的支持也越来越少。
西学的传播不应当是文化问题,从万历年间算起,中西互通在明清之际切切实实的走过一百年,甚至我们今天所担忧的,是西化的过快,而非过慢。
1722年的康熙意犹未尽,再度打猎,却染上风寒而死,皇四字在完全没有预兆的情况下匆忙登记,不久皇三子守陵,西学事业戛然而止。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席卷全球,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留给清王朝的,是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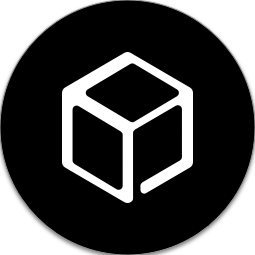

.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