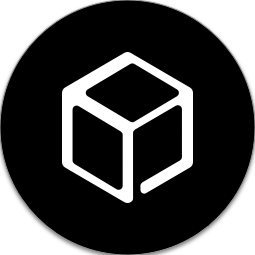.jpg)
读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不仅仅是一部制度史,更像一部关于制度与人心如何相互塑造、缠斗千年的长篇叙事。他以手术刀般的精准,剖析了贯穿中国政治史的两大核心命题:制度的生成与演变,人事的选择与博弈。这两条线索相互交织,共同编织出一部跌宕起伏、充满张力的历史长卷。
钱穆首先着眼于制度自身的逻辑。他指出,任何制度都不是凭空产生,而是“自根自生”,深深扎根于特定的历史文化土壤。汉代九卿制度的设置,便是这种“根生”逻辑的生动体现。这些名义上侍奉皇室的官职——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等,看似负责祭祀、礼仪、警卫、车马,实则承担着国家运转的枢纽职能。他们管理财政、司法、军事,甚至影响着官员选拔。这种“名实分离”的架构,折射出秦汉王朝“化家为国”的转型轨迹:从封建时代的贵族政治,走向帝制时代的集权官僚体系。但钱穆敏锐地捕捉到,制度文本的模糊性,为权力博弈埋下了伏笔。霍光辅政时期,宰相是否应参与“皇帝家事”的争议,正是制度设计与政治现实冲突的缩影。
唐代三省六部制的演变,则进一步展现了制度自身的生命周期。中书、门下、尚书“三权分立”的精巧构想,本意在于平衡皇权与相权,但在实践中却不断遭遇挑战。玄宗朝设立翰林学士草拟诏书,绕开了中书省的决策权;宋代将宰相的“熟拟”改成“面取进止”,进一步削弱了其话语权。钱穆强调,制度的完善并非一劳永逸,而是一个不断调试、适应的过程。他特别关注到科举制度的兴起与异化。科举本为打破门阀垄断、吸纳社会精英的创举,但在明清时期却逐渐走向僵化。八股取士、重形式轻实务的考试导向,最终培育出脱离现实的官僚群体。
如果说制度是历史的经纬,那么人心则是编织这部长卷的无形之手。钱穆深刻揭示出,制度的运行从来不是机械的,而是受到人的选择、观念、利益驱动的复杂过程。汉代察举制的初衷,是选拔“贤能”之士进入政府,打破贵族对权力的垄断。强调“德行”的标准,但在“乡举里选”的实际操作中,地方豪强的意见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一制度设计,无形中制造出新的权力寻租空间。
宋代王安石变法,则将“制度”与“人心”的冲突推向极致。王安石试图通过青苗法、免役法等新政,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但他的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遭到激烈反对。钱穆认为,王安石的失败,不仅在于策略失误,更在于他忽视了制度背后的人心向背。制度变革若不能获得广泛的社会共识,即便设计再精巧,也难逃失败的命运。
清代的统治更是将制度工具化的倾向发挥到极致,在看似沿袭明制的框架下,注入了“部族政治”的内核。六部尚书可单独向皇帝奏事,表面上扩大了言路,实则制造出官员间的相互监视;看似开放的科举考试中,设置了满汉名额的差异,确保了满族统治集团的优势;八旗驻防制度下,全国被纳入军事控制体系,汉人只能充当军事力量的辅助。而奏折制度的广泛应用,使得皇帝可以绕过正式的行政程序,直接获取信息、下达指令。钱穆对此的评价是,这种“密室政治”看似高效,实则暴露了制度正当性的缺失,最终走向“以人治代替法治”的困局。
综观钱穆对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得失的分析,他一方面强调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因时制宜”,与时代需求相适应;另一方面更强调制度背后的文化根基与人心向背。制度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设计,更取决于执行者的德行与能力,取决于整个社会的价值共识。正如他所言,要理解一个时代的政治,不能只看典章制度的条文,更要深入到其背后的人事网络与文化脉络之中。只有将制度、人事与文化三者结合起来考察,才能真正把握中国政治史的内在逻辑。